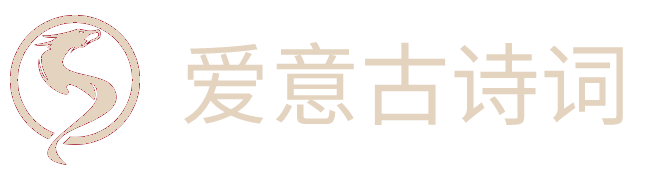杜甫,一位被人们认为总是愁眉不展的诗人,却因他那深邃的情感而在诗坛熠熠生辉。生活的压力与困境并没有让他消沉,反而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对人生、社会的思考与触动。他用笔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倾注其中,将自己的心灵痛苦化为艺术的表达。杜甫之诗,无论是饱含对社会不公的愤怒,还是流露出对人世沧桑的感慨,都令人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真挚情感。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才情与情感,杜甫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情感诗人,他的诗作至今仍然打动着人们的心灵。
文|黄薇杜甫对友人也一贯情真意切。比如最典型的他与李白的友情,惹得千年后还有读者为其“鸣不平”,认为这段友谊不对等,杜甫一片痴心付出太多。赤子心的杜甫,应该不会计较,他对朋友多是同情之理解,梁启超就说,“对于他们的境遇,所感痛苦,和自己亲受一样,所以做出来的诗,句句都带血带泪。”他对李白的深情人尽皆知,这里另外讲个小插曲。杜甫的名篇 《春日忆李白》,一开篇就是个爽利的判断句:“白也诗无敌,飘然思不群”,颔联接着写“清新庾开府,俊逸鲍参军”,古人夸人喜欢引名人作比,杜甫说李白的诗之清新俊逸,堪比南北朝的庾信和鲍照。不过李白本人对这个夸赞受用吗?很可能不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他最服膺的偶像毫无疑问是谢朓,“蓬莱文章建安骨,中间小谢又清发”;后人看得很明白,说他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,李白也没提过庾信鲍照这两位。作为李白诗歌的忠实读者、李白的迷弟兼挚友,杜甫不可能不知这一点。但这就是老杜的耿直,虽然天各一方没法当面纵饮论诗,也不管你听了开不开心,我还是要把想法说清楚;你最推崇谢朓,但我觉得你的风格更像庾信、鲍照。恰恰是杜甫的评语,成为后世一再引用的对李白诗歌的定调之论之一。此乃杜甫用情之真。

杜甫对普通民众的关爱自不待言。即使他写亲情诗,区别于众人的一大特点就是,写完个人际遇后总会忧己及人,宕开一笔再论时事,感情故总是百转千回、曲折回荡,是为“顿挫”之源。有几位学者都注意到杜甫一首平平无奇的七律《又呈吴郎》,“堂前扑枣任西邻,无食无儿一妇人。不为家贫宁有此,只缘恐惧转须亲。即防远客虽多事,使插疏篱却甚真。已诉征求贫到骨,正思戎马泪盈巾。”杜甫在夔州时为了更好地管理公田,自己搬到东屯,将瀼西草堂借给一个亲戚吴郎居住。他后来听闻这位吴郎在房子周围扎上篱笆,以防隔壁孤苦伶仃的寡妇来打枣,当下很是不快,于是有了这首委婉开导吴郎的诗。不过是念叨一件琐碎小事,仁者情怀涓滴不漏。此乃杜甫用情之细。
甚至还有学者专门论及杜甫对生物的泛爱,分析他诗中“民胞物与”的思想。杜甫会饶有兴味地描写无关宏旨的小动物们,诸如“鹅儿黄似酒,对酒爱新鹅。引颈嗔船逼,无行乱眼多”,天真而富情趣;也少不了《缚鸡行》这样宣扬仁爱的,“小奴缚鸡向市卖,鸡被缚急相喧争。家人厌鸡食虫蚁,未知鸡卖还遭烹。虫鸡于人何厚薄,吾叱奴人解其缚。鸡虫得失无时了,注目寒江倚山阁”,就是对动物生灵也不吝情义。
杜甫成为情圣的秘诀是什么?洪业说的是世界观——“他的诗篇,其最佳之处,不在措辞之壮美,铺排之工整,而在于他至情之表露:温柔敦厚,旭日春风。”梁启超说的方法论——“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‘半写实派’。他处处把自己主观的情感暴露,原不算写实派的作法。但如 《羌村》 《北征》等篇,多用第三者客观的资格,描写所观察得来的环境和别人情感,从极琐碎的断片详密刻画,确是近世写实派用的方法,所以可叫做半写实。这种作法,在中国文学界上,虽不敢说是杜工部首创,却可以说是杜工部用得最多而最妙。从前古乐府里头,虽然有些,但不如工部之描写入微。这类诗的好处在真,事愈写得详,真情愈发得透。我们熟读他,可以理会得‘真即是美’的道理。”
或许仇兆鳌总结得最到位:“非公至性,不能有此至情,非公至文,亦不能写此至性”,如此这般,成就千古情圣。